陕甘红军源起问题探究
作者: 梁晨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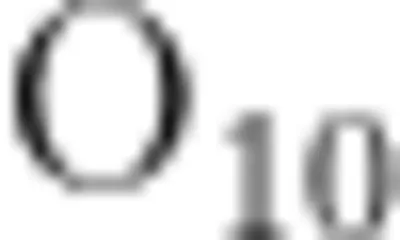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K263;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5)03-0016-11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西北地区共产党人经历曲折建军之路,组建起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为主力的陕甘红军。陕甘红军的成立为陕甘苏区的建立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陕甘苏区最终得以成为中央红军与南方各路红军的可靠落脚点和北上抗日出发点,陕甘红军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关于陕甘红军的研究也取得一些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①但之前研究或是仅以类似通史叙述的范式,对陕甘红军的形成与发展历程进行叙述,或是只涉及陕甘边红军的源起问题,未对陕甘地区红军源起进行整体探讨。实际上,陕甘苏区红军源起问题十分复杂。辛亥革命后的陕甘地区,国家权力处于失范状态,军阀混杂、赋税叠加、旱灾濒发,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导致农民自为暴动频发,民团、土匪、秘密社会不断出现。在这种复杂历史背景下,陕甘红军的源起与陕甘地方军事化系统有何关联性?中共陕西省委与刘志丹等人如何正视民团、土匪、秘密社会等地方军事化系统?陕甘红军源起过程中呈现的历史脉络与逻辑又如何?本文拟依托相关历史文献、未刊档案、口述访谈、地方文史、县志等资料,对陕甘红军源起问题略作梳理,希冀进一步深化对中共革命历史实践中地域特征的认识,揭示中共地方红军组建路径的异同之处,以期丰富对中共革命历史图景的认知。
一、20世纪初陕甘地方军事化系统的崛起
辛亥革命后的陕甘地区,农民生存境遇恶劣,国家权力处于失范状态,暴力成为日常,军事实力成为确立合法性的决定要素。军阀混战下的陕甘地区,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为争夺地盘与扩张势力,均就地筹饷,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如刘镇华督陕后,大开烟禁,强迫农民扩大种烟面积,并加大“烟亩罚款”的征收。①与陕北相邻的甘肃庆阳地区,从1922年到1928年的征税额度与税收项目变化巨大,征税额度从1922年的587.48元激增至1928年的175159.22元,税收项目也从一项增加到十项。②税额增幅如此之大,加速了农村经济破产和农民穷困。
苛捐杂税已使陕甘地区农民困苦不堪,而1928年至1930年的灾荒进一步导致陕甘农村经济崩溃。如甘肃庆阳地区属于干旱重灾区,颗粒未收,饥民载道,农民多以菜根树皮为食,甚至发生“易子而食”。③陕西安定县(子长县)井水全部枯竭,赤地千里,青草毫无,树皮草根均被采掘殆尽,“举村逃亡者不一而足”。④到1930年9月,陕西虽有降水,但由于“种麦太少”缘故,很多地区“有夏无收”,且农民大量逃亡外乡,农村地区“耕具全无,蒿草满目,间有耕者,草比牛高”。③因此连年旱灾导致陕甘地区农民生活雪上加霜。
由于军阀混战、赋税叠加、旱灾频发,20世纪初的陕甘农村经济崩溃、农民穷困。处于绝对困境状态下的农民个体与群体,其趋利性只能促使他们趋利避害实现利益优化,因此陕甘农民自为暴动日渐勃兴。1906年,为反抗清政府向陕西各县农民派征的路捐,扶风、渭南、华州以及蒲城、富平等州县农民发起规模巨大的抗捐运动。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民自为暴动日益激烈,如蒲城农民集合千余人反对“有奖公债”(陕西军阀的一种苛捐)。1928年陕甘地区出现严重旱灾后,农民暴动达到高潮。临潼交口镇农民因当地保安队强行搜麦,与其发生严重冲突,并将保安队缴械,“打死队兵十余人”,绥德农民有组织地向当地豪绅要粮。⑥
陕甘农民自为暴动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抵制军阀的肆意压榨,但连年灾荒不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而且进一步加剧农民的贫困化,造成过多饥民和流民。在地方政府无法有效对灾民进行救济与安置的情况下,个体的趋利性促使灾民开始自救,对军事力量的推崇以及迷信心理的催动,催生了陕甘地区民团、土匪、秘密社会等地方军事化系统建立与运行。尽管这些农民武装被地方政府视为非法团体,但在家破人亡的灾民看来,这是良好的“避难处”。
(一)民团
民团组织属于乡、区、县一级的军事组织。民国时期,土匪蜂起,散兵游勇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乡绅富户打出保境安民口号,纷纷组建民团,以保庄护财,抵抗兵匪袭扰,这类民团完全在豪绅地主掌握中,以保护地主阶级利益。据统计,到1930年前后,华池县境内活动的民团组织有:玉皇庙川民团、南梁民团等二十余股。①清涧县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影响较大的民团有:白秀珍民团、张云民团等九股。②庆阳地区到1931年前后,正宁县有民团十多股,合水县有民团二十余股。③这类被豪绅地主掌握的民团又成为地方军阀收编对象,例如陇东军阀谭世麟在华池县境内辖属的民团有:城壕民团、五蛟民团、悦乐民团、元城民团。④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旱灾影响,军阀粮款摊派日益繁重,土匪不断增多,陕甘地区一些农民自发组成民团,以抵御土匪侵扰。如正宁县各村为应对官府催粮派款与土匪袭扰,先后组织起“提民团”,当时有上五社、中五社、北八社、象东三社四个民团,团头分别是巩世信、张进选、杜兴邦、邢进友。这类民团组织组建后,农民仍在自己家中,一旦有紧急情况,几个团头相互商量后,以击鼓为号,将民团集中。③
综上可知,陕甘地区民团组织的构建,是陕甘地方权势人物与群体的因应需要。这些民团组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维护与强化社会治安的豪绅民团,另一类是抵御兵匪、反抗政府的农民自发民团。这些民团的建立与运行,标志着陕甘地区地方军事化的形成与强化。
(二)土匪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陕甘地区,匪患的规模及危害均有所增加。尤其是在渭北、临潼一带,土匪更多。1928年至1930年陕甘地区的旱灾,导致陕甘农民大批加入土匪队伍,陕甘土匪势力日益庞大。1930年4月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及,“而走险的土匪(大部是灾民)普遍全陕,总数约在十万以上,最近眉、凤、千、陇、宝、扶以及汉南、汉阴、山阳等地均为土匪占领”。除陕西外,甘肃地区土匪势力也不容小岘。如甘肃庆阳地区在20世纪20年代后同样土匪纷起,股多名杂,其中势力较大的土匪有:赵思忠股、陶玉山股等。①甘肃华池县境内盘踞和窜扰的土匪有薛大牛、毛不顺等52股之多。③土匪就这样成为陕甘地区社会与政治机体的构成元素。与陕甘当地民团相比,他们的装备更好,战斗意志更坚决。像那些收税的陕甘军阀一样,土匪也在自己的地盘上收取保护费。从各方面来说,他们无疑都是“有枪阶级”的一部分。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gdds20250302.pd原版全文
由于陕甘地区土匪势力较大,遂成为各方军阀和中共争取对象。正如有学者指出:“革命者显然不可能不被匪帮和秘密社团的革命潜力所吸引,他们的反抗是那么惹人注目,远远高于‘芸芸众生’。”①尤其对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中共陕西省委而言,急需将土匪这股强大势力纳人政治革命的洪流,以其强大的反叛力量来促进陕西革命运动的发展。但土匪自身作为灵活个体与群体,可以自主选择加入军阀或中共。随着土匪不断投靠陕甘地方军阀,导致地方军阀内部权力结构复杂且不稳定,继而影响到中共陕西省委的“兵运”工作。
(三)秘密社会
20世纪20年代中期,陕甘农村社会处于极端脆弱状态,并缺乏一种有效保障机制。应政治社会背景之需要,陕甘乡村地区一些秘密社会成为重要地方势力,如红枪会、哥老会等。
20世纪20年代初为抵抗在西北已蔓延开来、横行无忌的成群的土匪军队,陕甘地区红枪会活动兴起并日益活跃。1925年,红枪会由陕西传人甘肃庆阳、华池等地,由于红枪会具有区别于民团等组织的宗教色彩的显著特征,且红枪会还利用民间宗教的悠久传统,精心设计了一套引人注目的祈求神灵保佑的仪式②,因此在甘肃地区引起较大反响。如红枪会由陕西传入庆阳陇东各县后,农民纷纷加人,并以烧香敬神、结拜兄弟等形式在各地秘密组织红枪会③;在甘肃华池县境内,红枪会传入后,发展迅速,逐渐形成华池红枪会、温台红枪会等六股势力较大的红枪会组织。④
除红枪会外,陕甘地区的哥老会组织也较为兴盛。陕甘地区的哥老会组织是晚清时期,作为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带到当地的。辛亥革命后,陕西政局混乱,灾害连年,尤其在陕北的昆山、贺兰山等地,灾荒导致陕北农民经济破产,纷纷投入哥老会等组织,哥老会迅速发展,影响较大。③甘肃地区的哥老会组织自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主持甘政后,得到了较大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甘肃哥老会主要的山堂有中华山、五龙山、兴龙山等。
以红枪会、哥老会为代表的秘密社会在陕甘乡村逐渐兴起、发展与壮大,引起当时陕甘各派系注意。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后,便将“打人红枪会”、深人哥老会等秘密社会组织@,作为乡村农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希冀以中共革命理论指导红枪会等秘密社会,从而推动陕甘地区革命运动。
综上,20世纪初的陕甘乡村社会,农民自为暴动日渐勃兴,同时处于绝境的农民由于其趋利性,积极参加民团、土匪、秘密社会等农民武装。为解决武装生存问题,民团、土匪、秘密社会等武装也将收入来源指向农民,从而导致陕甘农民穷困程度日益加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恶性循环导致农民的绝对贫困,使民团、土匪、秘密社会等农民武装势力日渐庞大。由于此类农民武装是由迫于生计的农民组成,乡村朴素正义感依然存在,因此这些农民武装的政治倾向较为正面,从而使刘志丹等人后期联络、动员民团和农民武装参与中共革命活动成为可能。
事实上,不论是民团、土匪、秘密社会等农民武装,还是农民暴动,都拥有各自的组织首领,都是在其组织首领带领下进行活动,如民团首领是豪绅地主或者推选的“团头”,土匪有其各自首领,红枪会等秘密社会也有自身头目,农民暴动大部分也是在组织首领带领下进行统一行动。而这些组织首领往往会有一大批农民追随,尤其在陷入困境下,缺乏长远眼光的农民更加认为地方精英具有独特眼光,在其庇护下能够获取一定利益。因此地方精英顺理成章地成为民团、土匪、秘密社会、农民暴动的领袖人物,占据陕甘乡村社会核心位置,同时也成为各级军阀和中共努力争取的对象。
二、中共陕西省委及地方党部领导的“兵运”实践
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后,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经验的深度影响下,开始奉行以工农群众武装暴动并进行夺权为核心的革命方针。此后,随着中共中央政策由激进趋向和缓,中共陕西省委工作重心由“暴动”转向“兵运”。
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一系列暴动引起国民党陕西当局注意。1929年2月6日,中共陕西省委遭到国民党破坏,为继续推进相关工作,于同年3月紧急成立中共陕西临时省委。1929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陕西临时省委,应继续领导工、农、兵斗争,积极引导群众斗争向大范围发展,尤其重视士兵运动。①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新指示,改造了临时省委,加紧开展“兵运”工作。刘志丹和谢子长在中共陕西省委派遣下,从事的“兵运”工作主要是围绕改造陕甘军阀部队、土匪武装、民团武装三个方面进行,但前期主要是以争取、改造陕甘军阀部队为主。
1929年秋,刘志丹合法取得保安县民团领导权,将其成功转变为一支革命武装力量。1930年夏,刘志丹、谢子长打人甘肃庆阳军阀谭世麟部开展“兵运”工作。刘志丹利用其父刘培基与其友陈定邦(保安县公安局局长)提供的武器,将掌握的保安县民团一百余人与动员而来的农民,在保安县金汤镇编为一营,同年6月带领该武装进驻三道川,投往谭部。同时,谢子长、阎红彦通过“兵运”工作,从军阀杨庚武部带出周维琪营也到达三道川。土匪张廷芝率领其亲信也投靠了谭世麟。谭将三支武装合编为一个团,在刘志丹建议下,任命谢子长为团长,刘志丹、周维琪、张廷芝分任下辖三个营的营长。刘志丹深受谭世麟信任,被邀请前往谭的陇东民团军司令部,替其“主持”民团军整训,刘志丹借机进行“兵运”工作。正当刘志丹、谢子长伺机发动兵变时,投靠谭部的张廷芝收买了周维琪,在三道川设下圈套吞并了周维琪队伍,随后向谢子长团部和刘志丹营发动袭击,部队被打散,谢子长、刘志丹脱险后回到保安县。③这即是“三道川事件”,此次事件使刘、谢集结起来的武装损失殆尽,“兵运”工作受挫。
“三道川事件”后,1930年10月1日,刘志丹借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旗号,进驻合水县太白镇,之后集合骨干成员,成功收缴陇东民团第二十四营部分武装。③“太白收枪”后,刘志丹带领队伍到达合水县固城镇。当时在固城镇一带活动的农民武装主要有赵连璧(赵二娃)、唐青山、贾生财等。①赵连璧与刘志丹是姑舅亲戚,且赵连璧此人较为英勇,枪法准,南梁一带的民团、土匪都听其号令,先后收走太白民团、林金庙民团枪支,发展到一百余人,四十支枪。唐青山是合水县人,其部下大多是当地饥民,共有十几条枪。贾生财是横山县人,后逃荒到合水县蒿嘴铺,起初在陇东民团当兵,后组织起三四十人的民团,有十几条枪。赵、唐、贾三人与刘志丹关系十分密切,对刘较为敬重,希望能与刘部联合。刘志丹考虑后,同意逐步将其改造为革命武装。经过协商,一致推举刘志丹为总指挥,四支队伍改编后,共编四个连,有300多人。部队整编后,行军到盘克原一带,后与军阀陈珪璋部第五旅遭遇并激战,赵、唐、贾武装被击散,重回陕甘边界地区活动,刘志丹率部突围后到达小石崖一带休整,休整期间刘志丹派马锡五与当地罗连城民团建立统战关系,得到其援助,这也显示出刘志丹对于联系民团的重视。②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gdds20250302.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