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前期日本报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
作者: 卢晨 王有加【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5)03-0027-11
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率先发起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抵抗,这一系列革命举措引发了日本报界的持续关注与深度报道。这些报道一方面紧密结合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战略图谋,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抹黑报道与扭曲宣传;另一方面,又深刻剖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形势、政策制定与发展动向。马克思曾指出:“当报刊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①日本报界的报道正是这种“第三种权力”的典型体现,既服务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又反映了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复杂认知。近年来,学术界对域外视角下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政党形象进行了深入探讨。③这些研究均从不同角度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学术脉络。在此背景下,本文立足于前期成果《窥视与野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报刊对中央苏区报道研究》③的学术积累,通过对日本馆藏报刊文献的系统考辨,将观察视域从中央苏区的地域性聚焦拓展至对中共整体形象的认知建构分析,剖析日本报界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与日本“防苏反共”政策的历史关联,揭露日本报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负面宣传和舆论攻击,以期从域外视角充实对这一时期中共历史的研究。
一、日本报界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背景
日本报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根植于“防苏反共”的战略需要,这一需要既源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与同期中国苏维埃运动兴起密切相关。从日本国内看,20世纪20年代,日本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但财富分配极不均衡,工人和农民普遍面临贫困与剥削,社会不满情绪日益高涨。1922年,日本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成立,其纲领明确提出了“推翻天皇政府、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政治目标,①这直接触动了日本统治阶层的根本利益,日本政府将其定性为“受苏联操控的颠覆势力”。1931年,日本共产党中央常任委员市川正一在《日本共产党斗争小史》中指出:“日本资产阶级政府进行了对于共产党的大镇压。为什么要镇压呢?就是因为日本共产党提出支持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并且真正为这些口号来进行斗争”③。这一表述不仅揭示了日本共产党支持中国革命的态度,也反映了其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与全球无产阶级运动的紧密联系。同年,共产国际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人牛兰夫妇被国民党逮捕。据1931年9月18日《满洲日报》报道,牛兰的秘密文件中详细记录了“如何煽动工农,如何加入组织,如何进行党的训练,从而扰乱各国的政治”,其中特别提到“计划在中国苏区训练工农,派遣党员到朝鲜、安南、印度、日本煽动工人,以对日本和其他共产党的组织宣传训练”,③日本报界对牛兰事件的报道反映了政府对共产主义的警惕态度。1933年7月15日,《大阪朝日新闻》称设在日内瓦的欧洲反共组织呼呼日本加入,以“交换共产党信息、制定国际反共措施”。④日本对此积极响应,既源于对国内共产主义的担忧,也反映了其与西方反共势力结盟倾向。此外,该报还披露,中国、日本和美国海员通过红色秘密文件建立联系,形成“跨越太平洋的红色国际链条”。③这种跨国串联引起了日本政府的进一步警觉,鉴于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联系日益紧密,日本内务省决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在原有所谓“赤化”调查基础上,扩展至对苏联、中国、欧美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日本国内的学生运动、青年运动和共产国际的统一调查,③意图从源头上遏制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发展。这种由共产国际牵线搭桥的中日两国共产党多维互动促使日本报界将中国共产党视为“东亚赤化枢纽”,其报道框架逐渐从单纯的“中国问题”转向“威胁日本国家安全”的战略叙事。
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角度来看,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等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实践中,提出了将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的战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①这一战略调整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革命路径的深刻转变,也为后续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奠定基础。然而,因革命根据地位置偏远分散、信息不畅,加之国民党误导宣传,日媒当时普遍认为中共影响力大减。因此,1927到1928年,日媒报道虽提及中共,但聚焦分析其在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国民党反革命政变后中国政治走向。例如,1927年9月22日《大阪朝日新闻》的文章《共产党没落后的南方:今后是否稳定》②关注中国政局的不确定性;1928年5月29日《满洲日报》的《论述对华现状》③探讨中国各地时局;1928年9月24日《日本产业经济新闻》的《赤化运动的过程》④则回顾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演变。这一时期,日本报界并未将中国共产党视为主要威胁,而是将其活动置于中国内部政治变动的背景下进行审视,反映出其对中共实力判断的局限性。
随着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以及苏区版图的持续扩展,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壮大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利益构成了显著挑战。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迅速作出反应。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武装抗击日本侵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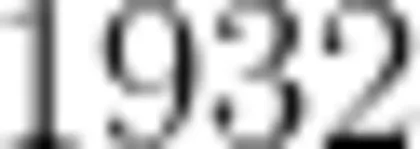 年4月1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宣布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6)4 月20日,红军占领漳州,随即成立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③这一系列事件促使日本方面重新评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5月10日,《东京日日新闻》发表社论指出,由于中共活动频繁,日本军方对其发展极为重视。特别是若中共扎根福建厦门,鉴于福建厦门与台湾的地理邻近性,不难预见中共的影响力将会辐射到台湾。③可见日本当局对中共势力扩张的担忧,更凸显了其对台湾防务的战略关切,显示出中国共产党活动的直接威胁已进人日本战略视野。同年12月18日,《大阪朝日新闻》进一步指出:“共产党有一个远大的计划,等待机会在东亚大陆横行霸道,各国必须组建阵营对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日本应为核心”。
年4月1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宣布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6)4 月20日,红军占领漳州,随即成立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③这一系列事件促使日本方面重新评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5月10日,《东京日日新闻》发表社论指出,由于中共活动频繁,日本军方对其发展极为重视。特别是若中共扎根福建厦门,鉴于福建厦门与台湾的地理邻近性,不难预见中共的影响力将会辐射到台湾。③可见日本当局对中共势力扩张的担忧,更凸显了其对台湾防务的战略关切,显示出中国共产党活动的直接威胁已进人日本战略视野。同年12月18日,《大阪朝日新闻》进一步指出:“共产党有一个远大的计划,等待机会在东亚大陆横行霸道,各国必须组建阵营对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日本应为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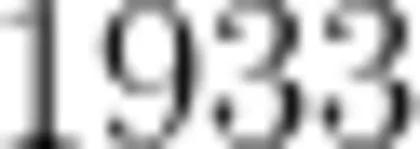 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事变次日,《大阪朝日新闻》的社论分析:“国民政府讨伐共军的阵营因福建的独立而完全崩溃,福建派与共军妥协,几乎处于同盟关系,共军将摆脱包围,获得休整和转战的机会”。@两天后,该报再次发文指出:“日本必须对台湾海峡对岸与中共结盟的新政权保持警惕,密切关注福建地区政治动向。”①
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事变次日,《大阪朝日新闻》的社论分析:“国民政府讨伐共军的阵营因福建的独立而完全崩溃,福建派与共军妥协,几乎处于同盟关系,共军将摆脱包围,获得休整和转战的机会”。@两天后,该报再次发文指出:“日本必须对台湾海峡对岸与中共结盟的新政权保持警惕,密切关注福建地区政治动向。”①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gdds20250303.pd原版全文
如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前期日本报界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并非偶然,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和防苏反共战略的产物。这些报道的背后,是日本政府和军部为维护在华利益、应对中共崛起和苏联影响所做的战略考量。从内容上看,日本对中共的态度经历了从低估到警惕的转变,其报道最终服务于为日本在东亚的战略部署提供情报支持和舆论准备。
二、侵略者的窥视:日本报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多维度观察
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报界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状况进行了多维审视。其报道聚焦于中共与农民阶层的互动关系、国共两党博弈以及军事力量演变等核心议题。日本报刊中对中共领导的苏维埃运动的分析和报道,既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视角下的战略焦虑,又能从中观察到中共领导土地革命的实践轨迹,形成了具有特殊史料价值的他者镜像。
(一)“真命天子”的降临:农村包围城市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与农民之间的紧密联系,是日本报界观察和报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视角。日本报界普遍认识到,农民不仅是革命的主体力量,更是中国共产党得以发展壮大的基础。《大阪朝日新闻》在1930年3月12日的《行进中的中国》一文中指出:“中国真正的革命是从农村开始的。”①在这一背景下,日本记者神尾茂在1931年1月15日的报道中进一步分析称:“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引导农民阶级走向革命斗争的前线,是超越国民党以民生主义为基础的农民运动。”②这一论断表明,日本观察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并非单纯依靠暴力,而是通过组织和动员农民,使他们成为革命的主体。同年6月19日,《满洲日报》的分析更进一步,指出土地革命的核心目标是让农民摆脱经济、政治、社会和自然的束缚,实现真正的解放。然而,由于封建制度的长期压迫,农民难以单独完成这一转变,因此他们寄希望于一个能够带来土地分配和社会变革的“真命天子”③,而中国共产党正是扮演了这一角色。
“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提出,正是基于农民在革命中的核心地位。日本记者日森虎雄观察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并非单纯追求对城镇的占领,他分析:“红军游击队的目的是破坏旧社会的组织,获得武装和粮食,并进行共产主义的广泛宣传。”④这表明日本记者认识到,中共正在进行一场持久的社会改造和政治构建,而非短暂的军事冒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的应对策略,《满洲日报》曾在报道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若不制定“进步的农民政策”,就无法根除红军赖以生存的土壤,因为“农民战争的起因仍然是在农村,左翼运动的沃土仍然是在那里展开的”③。这凸显了日本观察者眼中,国共两党在理解和应对中国核心问题——农民问题上的根本差异。《大阪每日新闻》的报道更具体地描绘了中共如何利用国民党的失误赢得民心的策略,“通过打击地主富农和贪官污吏,将土地和财产转移给贫农,即使征收税赋也远轻于地主剥削,从而轻易获得农民的支持和情报,‘苏联万岁’‘共军万岁’成为农民‘趋利避害’的口号”①。可见中共政策的实用主义面向及其动员效果,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吸引农民,更在物质利益上满足了农民的基本诉求。
对于中共土地政策的具体内容,日本报界亦有关注。《日本产业经济新闻》1931年4月7日的报道指出:“在经济方面,没收田地,烧毁土地契约书,将全县土地分给半自耕农、农业佣人、佃农,其余作为苏维埃公田,让农民耕种,收获三分之二归政府,三分之一由农夫获得,土地税则是根据各人各年收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多寡而定税额。”②这一政策的实施,赢得了苏区农民的广泛支持,使得共产党在农村的治理得到巩固。松谷与二郎在1933年9月4日的《东京时事新报》中进一步强调,红军在短短四年内迅速发展,关键原因在于其土地政策切实惠及农民。他指出:“共产党军队没有进行任何掠夺,他们在占领的土地上驱逐了地主,并将土地按照比例分配给贫农。”③这种分析超越了简单的敌对宣传,承认了中共政策在争取农民方面的实际效果,并将其视为中共军事力量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关键。相较之下,国民党在“白区”推行的苛政则加剧了农民的不满。例如,《大阪每日新闻》1933年6月21日的报道提到,“熊式辉的江西当局由于财政困难,对红军占领的剩下三分之一地方的疲惫农民横征暴敛,农民们自然怨恨中央政府,转而接待共产党军队”④。在当时的日本观察者看来,民心向背,尤其是在关键的农村地区,已经成为决定国共力量消长的核心因素,而土地政策正是争夺民心的主战场。
除了土地革命,日本报界还注意到中共在农民教育方面的努力,其中的报道大体上比较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大阪朝日新闻》1931年1月5日的《明天的中国》一文指出,中国 85% 的人口是文盲农民,这一群体的文化觉醒将决定中国革命的未来③。中共敏锐地把握了这一关键问题,通过开展革命思想教育对农民进行文化启蒙与政治动员。风间阜在《日本产业经济新闻》1931年4月3日的报道中提到,共产党高度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红军占领地区的学校被改为“列宁学校”,专门教授革命理论@。日本南满铁道公司也在调查中提到:“妇女、青年以及广大群众也从数十年的封建奴役中解放出来,享受自由和平等的生活。此外,政府还建立了农民银行,为农民提供资金,消除了高利贷,并创办了列宁学校,让儿童能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③此外,思想改造的成果还体现在宗教信仰的转变上。“神庙变成了列宁学校,虽然老爷老太有些还信仰佛教,但是在青年男女之间基本上是消失殆尽了。”③可见,日本报界对中共在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政策已有较深人的观察,并认识到这些政策是中共得以壮大的关键因素。
(二)伸向远东的“红色魔爪”:窥视中的国共对峙
1930年至1934年间,国民党先后发动五次大规模“围剿”行动,意在彻底“剿灭”苏区政权;而中国共产党则凭借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多次突破敌方的军事封锁。这一时期,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军事冲突,成为日本报界重点关注的视角。在日本报界的报道中,中国共产党常被渲染为“伸向远东的红色魔爪”,折射出当时日本社会对中共发展的深切警惕与担忧。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gdds20250303.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