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救灾的实际运作
作者: 曹佐燕【中图分类号】k27: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5)03-0061-14
传统中国灾荒关乎天命,救灾攸关灾民生死和政权合法性。历代政府均注重救灾备荒,基本形成以政府救济为主、民间赈济为辅、灾民被动等待、旨在维护统治秩序的传统救灾模式。及至封建王朝末期及民国时期,政府难以统合全国救灾资源,随之救荒机制衰败、救灾乏力、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有效整合政府的救济、社会的互助和民众的生产自救,开创一条通过恢复和发展生产来救灾渡荒的生产救灾新路径。①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省五莲县属于轻灾区,积极贯彻生产救灾工作。这与同期全国的灾害强度和救灾方式相近,大致可视为全国救灾的缩影。有鉴于此,本文以山东省五莲县为例,深入体察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救灾的实际运作。
一、“不饿死一个人”:政治合法性与治理能力的张力
1949年全国相继发生旱、虫、风、雹、水等灾,受灾人口约4555万人,倒塌房屋234余万间,∗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海河流域生产救灾史(1942-1983)”(23LSA0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目前学界理解的生产救灾几乎等同于临灾救济,忽视了生产与救灾密切结合的内在要求。中国内地的中共救灾研究成果主要遵循“严重灾荒—政府救灾—巨大成绩”的论述模式,大致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侧重地方的灾害应对研究,旨在论证中共强大的救灾能力;另一类是跳出地域视角,将救灾纳入社会救助和乡村救济中。后一类研究虽然有意从临灾救济的角度来论述生产救灾,但与其他学者论述的生产救灾基本相同,这再次说明学界理解的生产救灾等同于临灾救济。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救灾研究成果中尤为明显。前一类的成果有石武英:《湖北省抗洪救灾研究(1949—195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王瑞芳:《从点到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淮河治理》,《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9期。后一类的参见高冬梅:《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与实践研究(1949—1956)》,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李小尉:《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社会救助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谢迪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救济理论与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减产粮食114亿斤。①由于生产力低下、连年灾荒加之长期战争的资源汲取,民众几无储蓄,抵抗灾荒能力薄弱。1949年冬季七八百万人已经断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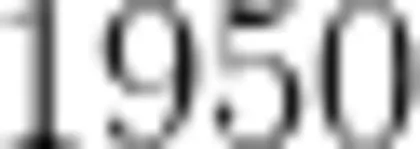 年全国灾荒延续且日益深重,春荒人口高达4920万。③灾民深陷缺粮、缺草、缺盐、缺衣、缺办法、有病的“五缺一有”的惨状,饥饿难耐之际甚至卖妻鬻子、吃观音土,坦言“只要石头挡饿也要吃”。④绝望情绪蔓延,大量民众逃荒、集体乞讨、明抢暗偷,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灾荒成为政府急需解决的难题。
年全国灾荒延续且日益深重,春荒人口高达4920万。③灾民深陷缺粮、缺草、缺盐、缺衣、缺办法、有病的“五缺一有”的惨状,饥饿难耐之际甚至卖妻鬻子、吃观音土,坦言“只要石头挡饿也要吃”。④绝望情绪蔓延,大量民众逃荒、集体乞讨、明抢暗偷,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灾荒成为政府急需解决的难题。
灾荒既考验着中共的全国执政能力,攸关政府信誉和国际观瞻,也是塑造政权新形象与合法性的“天赐良机”。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便向各级政府下达“不俄死一个人”的政治任务。严峻灾荒之下饿死人似乎在所难免,若有意外难免有损政府威信,加之“不饿死一个人”似乎不分阶级,内含极大的物质投入需求,因此该任务饱受质疑。刘少奇对此直言“我们如果不敢提出‘不许饿死一个人’的要求,那我们还算什么人民政府?”⑤是否饿死人攸关政府形象,毛泽东、陈云、薄一波、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求各级政府保证完成“不饿死一个人”的政治任务。内务部部长谢觉哉指示将以奖惩方式对待能否完成“不饿死一个人”任务的各级政府。 (6)1949 年12月20日华东局指示各地尽一切可能做到不饿死人。③山东省为此决定实行各级负责制。五莲县对“不饿死一个人”的政治任务实现“按级负责”,一直下达到村干部。③
与以政府救济为主的传统救灾不同,中央和各级灾区政府要求各地完成“不饿死一个人”的政治任务,却确立以自救自助为基础的救济政策。该救济政策是意识形态和国际地位的考虑、财政需求的客观要求、事实情况的主观认定等综合作用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公然宣称没有一个中国政府成功解决民众的吃饭问题。有鉴于此,中央有意通过救灾向全球展现新形象,彻底改变清季民国积极接受外援的态度,强调灾民依靠自救自助,“不要外国一粒粮食的救济”。@中央救济政策立足于灾民自救自助,显然是相信民众有粮和具有自救能力。中央洞悉农民的生存理性和生活习性,指出农民吃粮本有弹性,“粮贵就会吃少、吃粗、吃稀”,灾荒之际可以吃糠咽菜,少吃粮食。青黄不接之际陈云认为灾民多有存粮,①内务部着重提到“新区储粮者尚多”。②
中央确立以自救自助为基础的救济政策,也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确定各自的救灾方针。为应对程度不一的灾荒,各地的具体救灾方针大同小异,均强调自救自助。③从华东局、山东分局直到胶东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救灾方针均是“生产自救、社会互济为主,政府扶持为辅”。但实际运作过程中社会互济容易发生强迫命令行为,出现大量高利贷现象。能放贷的人多出自有余粮的家庭,这部分人主要是乡、村干部。他们带头放高利贷。与此同时,“部份[分」区、村合作社发放高利(贷)成为主要营叶[业]”。①乡、村干部和合作社的定位都是为人民服务,而放高利贷行为显然不符合他们的职责定位。五莲县委决定强力制止高利贷现象,修订了救灾方针,强调以生产自救为主。虽然高利贷代价高昂,但是没有高利贷却削弱了救灾力量,最后酿成救灾工作的严重失误,短时间内出现6人非正常死亡现象。两害相权取其轻。灾民、乡村干部和合作社都强烈不满制止高利贷行为。有鉴于此,1950年3月18日五莲县委将“生产自救为主,社会互济、政府扶持为辅”的救灾方针改定为“生产自救、社会互济为主,政府扶持为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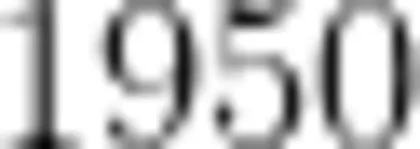 年4月5日,五莲县委就病冻饿死人的检讨中认为上级制定的“生产自救与社会互济为主,政府扶持为辅”才是正确的救灾方针。③这就明确否认此前的救灾政策,再次肯定社会互济,但生产自救依旧是救灾政策的核心。
年4月5日,五莲县委就病冻饿死人的检讨中认为上级制定的“生产自救与社会互济为主,政府扶持为辅”才是正确的救灾方针。③这就明确否认此前的救灾政策,再次肯定社会互济,但生产自救依旧是救灾政策的核心。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gdds20250306.pd原版全文
五莲县强调自救自助,还形成一套严格的运作机制。首先是整顿思想,从思想上说明人定胜天和积极生产可以战胜灾荒。对于基层干部,县委号召检查思想作风,严厉批评对生产自救没有信心的思想,将领导生产自救的情况视为干部党性的试金石。对于灾民,则是进行时事、前途、阶级和回忆对比教育,说明“过了荒年有兆年,荒年不久即过去”,批评听天由命、靠天吃饭思想,确立生产自救的信心。其次是宣布具体救灾方法,五莲县基本划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是帮助困难户打生产自救谱(搞副业种菜等);第二步,宣传自由借贷,亲邻相助;第三是到实在没有办法的关头,在[再」社会互济,这样就饿不死人”。④一言以蔽之,五莲县要求基层干部和灾民从思想上彻底祛除对政府救济的期待,首先尽可能地充分挖掘灾民“自己救自己”的信心和潜力,其次在实在无计可施之际才依次开展自由借贷和社会互济,最后才是政府在春节前后、青黄不接之际等特定时期主动发放救济粮。鉴于多次意外事件,五莲县虽历经政策变更,但始终强调自救自助,针对特定的救灾对象亦有严格的政策实施顺序,践行自救为主、互助为辅的方针。
社会互济和自由借贷均有严格的条件限定,广大灾民被鼓励采取的措施几乎只剩下生产自救。基层干部就如何领导灾民开展生产自救基本束手无策,被五莲县委批评为“多是空喊自救,缺乏具体办法”。③事实上,面对严峻灾荒,五莲县委对生产自救亦是“无信心、没有办法”。灾民能否通过生产自救渡过灾荒,攸关基层干部能否完成“不饿死一个人”的政治任务。基层干部为完成“不饿死一个人”政治任务,要求放开政策限制和加大政府救济,被五莲县委斥责为“不相信群众自己起来救自己的伟大力量”。③大量基层干部根本不相信生产可以自救,因而各地干部普遍怕做生产救灾工作。50名脱产干部回家意愿极为强烈,不惜借口有病甚至不干工作直接回家,③数目之多竟达到县区干部的近十分之一。①这些现象并非五莲县独有,整个山东省都出现这种状况。1950年4月10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郭子化发现“自提出生产救灾不荒地不饿死人,实行各级负责制以后,各地若干干部因而害怕荒了地、饿死了人自己负责不起,不想作生(产)救(灾)工作”。②
从中央、华东局、山东省、胶东地区直至五莲县均强调自救自助,力图充分挖掘灾民生产自救的潜力,缓解社会互济引发的秩序震荡,尽量减轻政府救济压力。五莲县曾就是否提倡社会互济几经反复,其实这不过是各地的缩影,旨在破除各地灾民和干部依赖政府救济的思想。华东各地虽然提倡生产自救与社会互济为主,但是在实际贯彻中几乎都首先侧重生产自救,其次才是社会互济,且要求社会互济乃灾民自救力量耗尽的急救之策。从传统时代走来的广大灾民和基层干部对于生产自救颇为陌生且难有信心,有意无意地关注社会互济,于是各地为了贯彻落实生产自救,对社会互济亦有时间限制。除社会互济可能滋生侵犯中农利益等弊端外,各地不惜限制社会互济以强调生产自救,既是应对灾区干部不相信生产自救的教育措施,也是财政困境下的现实要求。
二、生产与救灾:国家意志的内在张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收人的增加很大程度上依赖公粮的增加。为完成不断增加的公粮任务,粮食增产的任务也不断增加。1949年底中央制订100亿斤的粮食增产目标,随后加到144亿斤。③中央把增产数据细分到各大区,各省市将增产数据层层下分,最终五莲县接到每亩14斤的增产指标。④五莲县向各区下达每亩15斤的增产要求。③五莲县委指示生产救灾是实现1950年增产目标的关键,要求“一切措施皆为了增产”。⑥一方面要成功救治灾荒,完成“不饿死一个人”的政治任务;另一方面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增产和保障公粮收入。这本身是极具挑战的难题。
生产自救的生产大致可分为农业生产与副业生产。灾民最重要的生产自救措施本是副业生产,但五莲县委强调副业生产是末,农业生产才是本。冬荒期间,五莲县重点开展固定代耕和积肥运动,强调副业生产要与春耕准备结合起来,鼓励开展利于“沤土攒粪”的副业。③春耕伊始,五莲县明确要求以农业生产为主,结合副业生产,严厉批评因副业生产而影响、忽视春耕生产的行为。1950年5月9日县委总结春季生产救灾的主要经验是自春以来始终强调农业生产。③
面对生产与救灾之间难以避免的冲突,五莲县明确指示“生产也即是救灾”,③提出“生产不忘救灾,救灾为了生产”,①具体的救灾措施是号召家家打谱渡荒,人人生产自救。为落实从农业增产来救灾渡荒,五莲县要求各地不荒地,将“不荒一亩地”与“不饿死一个人”并列为政治任务,②基本延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荒一亩地才能做到不饿死一个人”③的思想。“不荒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的政治任务又侧重“不荒一亩地”,以此来弥合生产与救灾之间的张力。
1950年2月春耕生产还未全面展开,五莲县上报生产救灾工作时,其全称已是春耕生产救灾渡荒。此时五莲县高度重视春耕生产。农业生产需要稳定劳动力持续投入生产,而耕畜是春耕生产的主要动力。防止逃荒和保护耕畜对农业增产不可或缺,亦成为五莲县的政治任务。春荒期间五莲县反复要求执行按级负责制,保证完成“不减少牲口、不逃荒”的政治任务。④
1950年3月18日春耕全面铺开,五莲县委全力突击春耕春种工作。春耕要求民众长时间体力劳动,饥饿之际民众实无力春耕春种。“在灾民饥饿不能劳动,妨碍春耕春种的情况下,则政府采取紧急措施给以必要的扶持是能起头等作用的”。③为了让失去自救能力的灾民“不误生产”,五莲县发放土改以来的果实尾巴,还提供救济粮13万斤。五莲县救济粮严格限制发放对象,对于地主、富农、懒汉、二流子,春耕准备期间五莲县奉行不生产者不救济。对于害怕饿死的懒汉、二流子群体,五莲县委明确要求“强制其参加生产,绝不能置之不问”。③通过奖惩管理灾民,五莲县提升灾区春耕生产积极性。
五莲县通过发放物资、组织动员、宣传教育多措并举,发动积极分子,从典型到一般全面推动春耕运动。大年初一洪凝区村民开始拾草,初二街头区村民拾石头、修春地。正月初三中至区村民开始春耕。③惊蛰前五莲县春耕已成风潮,而五莲区作为全县最晚耕种地区,也在谷雨前耕完春地。整个五莲县的春耕进度比1949年提前5天至10天。③这在时间上保证适时耕种。五莲县委还下派干部检查荒田情况,最终基本完成不荒地任务,这恰是全国的缩影。1950年5月31日春耕结束之际,山东省人民政府回顾指出此时已基本完成不荒地任务。1950年山东省和华东区的耕地面积分别是12922万亩、34494万亩,但粮食播种面积均明显超额,分别达到16950万亩、45423万亩。⑪1950年7月内务部陈其瑷副部长指出“与历史上灾后田园荒芜赤地千里的景象相反,绝大部分被淹田地排水之后都补种上了,有些地区甚至还新开了不少耕地”。②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gdds20250306.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