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冲樽俎:中共借力军调部达成东纵北撤
作者: 叶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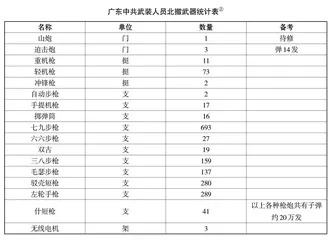
【摘 要】东江纵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在全民族抗战期间曾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多次重兵“围剿”。抗战结束后,中共在重庆谈判中承诺撤出包括广东在内的南方八个解放区,然而东江纵队此时却面临生存危机。国民党当局宣称,华南并无中共武装,只有“土匪”,并调集重兵试图短期内消灭东江纵队。在此危急时刻,中共一方面利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这一公开机构争取有利谈判条件,力争派出第八执行小组赴广州监督停战及撤军的执行情况;另一方面则利用美国表面上“公正”的立场,通过美方向国民党方面施压,最终迫使其作出让步。经过一番唇枪舌战,折冲樽俎,最终东江纵队顺利北撤,保存了东江纵队这支革命武装的主力。
【关键词】军调部;广州;执行小组;东江纵队;北撤
【中图分类号】K26; 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6-0083-15
全民族抗战中后期,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渐趋激化。美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派遣赫尔利来华调停。抗战胜利后,国共冲突频发,受降权是引发冲突的重要问题。重庆谈判与双十协定的签订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共矛盾,相反冲突在加剧。赫尔利辞职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马歇尔为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冲突。马歇尔使华的重要产物就是组织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或执行部),作为监督国共停战等一系列事宜的执行机构。由于国共两党在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发展道路等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以及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发动内战,军调部最终未能阻止中国全面内战的爆发,但是在一些具体事务上还是达成了目标比如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东江纵队北撤。由于资料不足,目前学界关于军调部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主要集中在军调部成立的背景、组织、与美国的关系以及某些具体活动等。近年来有学者对中共在东江纵队北撤政策的变化和美国调处东江纵队北撤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由于没有充分挖掘使用国民党方面的原始档案,对一些问题尚未揭示清楚。就军调部与东江纵队北撤问题而言,首先产生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在已经达成协议的问题上,国民党方面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设置障碍?此外,军调部这个机构,在调查监督停战问题上,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中共最终又是如何促成东江纵队北撤任务完成的?本文拟使用相关档案、日记、回忆录等史料,对军调部广州第八执行小组以及东江纵队北撤谈判过程作一梳理,以期深化对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关系等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一、东江纵队北撤问题的由来
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重庆谈判中,中共明确承诺将撤出包括广东在内的南方八个解放区。然而,国民党方面无意履约,试图压缩直至消灭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具体到广东,国民党当局借口广东没有中共武装,以“剿匪”为名,公开向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从而引发了东江纵队能否安全北撤的问题。
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抗战胜利后中共在政治上的一系列主张。8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表示为了争取战后和平建国,准备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让步,“我们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要在谈判中看看”。可见,中共对于重庆谈判作出了让步预案,撤出包括广东在内的南方解放区在拟议之中。
重庆谈判虽有前景,但也密布荆棘。经过国共两党代表的艰苦谈判,最终在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9日,蒋介石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明确表示:“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也就是说,蒋介石希望中共交出武装,以换取“和平”。毛泽东回到延安后针锋相对地给各中央局以及各区党委发电报表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鄂、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而且“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可见,虽然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但是众所期待的国内和平并未到来。
鉴于国民党当局并未表达和平建国的诚意,中共中央要求广东党组织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和平谈判上。8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中,对广东这种敌我力量对比处于劣势的地区的斗争策略指示道:“必须独立地分析环境,解决问题,冲破困难,获得生存和发展。待到国民党对于你们无可奈何的时候,可能在两党谈判中被迫承认你们的力量,而允许作有利双方的处置。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
尽管中共在谈判中预备在广东作出让步,撤出广东的人民武装,但是国民党方面采取的却是加紧“清剿”的政策。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的张发奎认为“必须使用武力处置广东的共产党部队”,“同时拟订全面解决的办法”。对于国民党当局的图谋,中共中央要求广东区党委以分散游击的策略加以应对。9月10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电广东区党委书记、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及广东区党委,指示斗争策略:“应迅速讨论并计划分散坚持的办法,即将主力部队分散成数十股,每股几十人至几百人,利用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及东江、北江、西江各地大山及闽西、闽南的群众基础,分散转移,与采用秘密方法去坚持斗争。其余小部则原地就地坚持,很好组织两面派的斗争,并分散大批人员到城市工作”。东江纵队据此进行分散,以应对国民党军的进攻。
虽然广东区党委以及东江纵队已经做了一些准备,但是在国民军的大举进攻面前仍然遭到了较大损失。10月15日,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得到情报,张发奎在广州召开“两广绥靖会议”,要求限期三个月将广东的中共武装“清剿”完毕。10月17日,尹林平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表示:“各地均遭顽军之进攻,粤北自申佳(九月九日)起,受一六〇师进攻,我伤亡损失百余人,北支自未酉(八月二十五日)起,受一五二师等进攻,伤亡失散亦百余人,西北支队,自九月初北上受顽截击后,即断联络,至今不明情况。东江区,自申虞(九月七日)起,内战迄今未停止,现新一军又进攻惠阳、龙岗、坪山、淡水一带,我尚无大损失。潮梅及韩江亦不断在战斗中。”为了坚持斗争,并减少损失,10月19日,中共中央回电同意广东区党委分散坚持的部署,表示:“为要隐蔽,必须以连排为单位分散行动,一区数百武装不〔必〕须分成许多小股行动,依靠群众、地形、党的基础、统一战线的关系等,利用敌人内部矛盾,采用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斗争手段是能存在和发展的。”
此后,东江纵队各部仍不断遭到国民党军的攻击。1945年12月30日,曾生、尹林平向中央军委报告称:自12月7日以来,国民党动用新一军三个师、五十四军第八师等四个正规师,并结合地方团队和伪军,“对我重重包围,严密封锁,分兵住守圩堰及各个大的村庄和山道及通路的村庄,构筑工事,我江南指挥部与其完全失去联络,并损失极大”。为了打破“清剿”,广东区党委决定采取以下措施:主力部队立即向惠紫突围,开辟新区域,接应其他部队;“每个小区域组织数个武工队和海队”,发动群众,坚持斗争;“精简目前不必要之人员,保存干部,适当安置英界及其他地方”;“干部分散负责”等。与此同时,海南岛的局势也十分险恶,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上岛后,“便一面紧张地进行劫收,另方面伪装和平面孔,放出和平空气,企图麻痹我们,并疯狂地布置内战阴谋,企图乘我无备,一举歼灭我主力和领导机关”。琼崖纵队一方面根据双十协定的精神,积极主张实现全面和平;另一方面做好保卫根据地的作战准备。在严峻形势下,广东区党委甚至准备迁到香港工作。
针对如此险恶的局面,中共中央要求广东各级党组织努力克服困难,坚持斗争。11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琼崖特委,指出:“琼崖党政军民,正面临着一个大的残酷的斗争”。1946年1月2日,中共中央致电尹林平、曾生,告诉他们“和平局势大体可定,惟达到和平还会有曲折,还须经过严重的斗争”,因此要“依靠你们自己力量和各种灵活的去领导当前的斗争”。对于广东党组织的困难,中共中央已经知晓,并将在与国民党方面的停战谈判中严正提出,要求其“停止军事进攻”。“只要你们熬过当前二三个月,可能改变这种困境”。
在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面前,东江纵队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了自卫反击。东江纵队在路东区的大鹏湾一带与国民党军“剧战延续到正月十日”,最终将国民党军“击退”。在粤北,“鸡公田、石壁围之役,我队被迫自卫抵抗,双方死伤甚重,国民党内战军死伤团长、团副各一名,其余军官五名,士兵一百五十名”。这样,国民党当局想通过“清剿”消灭广东中共武装,造成既成事实,以不履行双十协定的企图就破产了。
国民党当局否认东江纵队这样一支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的人民武装的存在,并将其诬为“土匪”加以“剿灭”,首先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再加上,抗战胜利后国内外普遍要求和平,国民党当局不断发动对东江纵队的进攻,本身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自然会面临巨大压力。面对危机,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广东区党委及东江纵队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努力保存了自身力量。
二、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的派遣与初期调处的挫折
东江纵队北撤问题的解决,与当时国共关系的总体格局和美国的介入是密切相关的。军调部是马歇尔来华后成立的调处国共冲突的机构,经过双方数次商讨,最终决定派遣执行小组赴广东解决东江纵队北撤的问题。但国民党方面设置重重障碍,阻挠执行小组的调查和处置,造成广州执行小组无法正常运转。
1945年12月27日,国共谈判恢复。周恩来将中共代表团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交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此时,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公报,重申不干涉中国内部的事务。在这样有利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周恩来和王世杰谈判。对于中共方面的提议,国民党方面表示:同意停止一切军事冲突,组织军事考察团,对所有同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受降有关的事项,由国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商定办法。1946年1月1日,马歇尔提出设一机构处理有关的一切具体问题,下设四个交通中心、八个小组。5日,周恩来和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同张群、王世杰、邵力子谈判,拟定《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
1月11日,军调部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组成并于13日赴北平工作。军调部由国、共、美三方各出一名委员组成,其下设置执行组,督察向有关部队发布及传达一切命令、指示及训令,并可设立分站,派遣监察及报告小组。执行小组前往调查地点由美方代表以主席名义拟定并由三方一致同意,如果有一方不同意,则上报军调部三委员以及三人会议。小组中讨论的内容、提交的材料以及报告也需三方一致同意,否则提交联合参谋长会议处理。
根据重庆三人会议要求,“执行部最高首脑为三委员,其下三方各有执行科科长”。执行处“根据执行部主任委员之政策及决议,拟定计划提请委员会批准后执行”,具体“由联合参谋组执行之”。军调部各小组的派出由三委员在执行部委员会议讨论,由执行处分配任务,主要负责监督停战令的执行,联合参谋长会议讨论各小组无法解决的问题,由三委员的执行部委员会议进行最终裁定。如三委员在执行部委员会议无法裁定,则提交三人会议仲裁。
向广东派遣执行小组符合上述原则,但此举遭到国民党方面的阻挠,引发军调部国共双方争论。在1月19日召开的执行部委员会议中,中共代表提出要执行部介入解决广东国民党军与东江纵队在东江地区的冲突。美方执行处处长海斯克上校表示可以考虑。国民党代表蔡文治则提出执行部之职权能否达到长江以南的疑问。对此,叶剑英回应,除东北外,中国境内所有有冲突之处,均在执行部工作范围之内。叶剑英随即提出,是否即可决定派一小组至广州地区。郑介民以集宁问题应较广州问题优先讨论为借口进行搪塞。柏路德上校追问是否派小组,郑介民试图岔开话题。最后,柏路德上校明确表示可派小组赴广州,并可由各参谋长先行讨论。海斯克上校则提议在次日召开的会议中讨论。由此可见,国民党方面和美方在广东停战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这为中共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如能善加运用,当可在一定程度上制止国民党方面的过分无理之举。
就在军调部讨论是否向广州派遣执行小组时,蒋介石指示张发奎、罗卓英称:“如北平军事调处执行总部派员来粤调处冲突时,兄等应以粤省本无共军亦无冲突事,而且总协定规定在长江以南区域并无调处之职责。故当执行组到达时可婉辞拒绝,不予陪送。”张发奎据此对执行小组代表声称,广东除少数“土匪”外,根本无中共部队,更不知所谓东江纵队等番号。中共提出双十协定包含广东区,张发奎亦予以否认。美国代表米勒上校坚持要去各地视察,蒋介石令张发奎婉辞拒绝。国民党方面最终同意向广东派遣执行小组,只是为了敷衍美方,并不是为了真正解决问题。在第八执行小组到达广州的当天,国民党军调部执行委员郑介民致电蒋介石表示:“关于广东派遣执行小组,因共党屡称国军在该方面欲消灭共军。经职反驳,但美委员对于停战命令之解释,以长江以南及东北九省,可有军事调动,但停战系全国停战。职为表示我对于停战之诚意,对美委员每次主张,均予接受。但经提出保留,如该组视察后,该方面无冲突时,应即撤回。”次日,郑介民再次致电蒋介石,声称:“派粤小组职曾经反对,僵持二天不决。后美方称停战命令包括全国,广东不能除外。且美方望停战甚切,主张坚决,我方为表示诚意,乃同意派小组往粤。惟职已嘱派往参谋报告向华主任:(甲)设法拖延;(乙)说明为民团与匪冲突。”作为军调部执行委员的郑介民,对广东局势并无调解之意,反而试图从停战令生效范围、广东有无中共武装以及有无冲突等方面,给广东国民党当局出主意,以拖延执行小组行使职权。这充分表明,广州第八执行小组面临的局势是复杂的,完成任务的前景也是困难重重的。